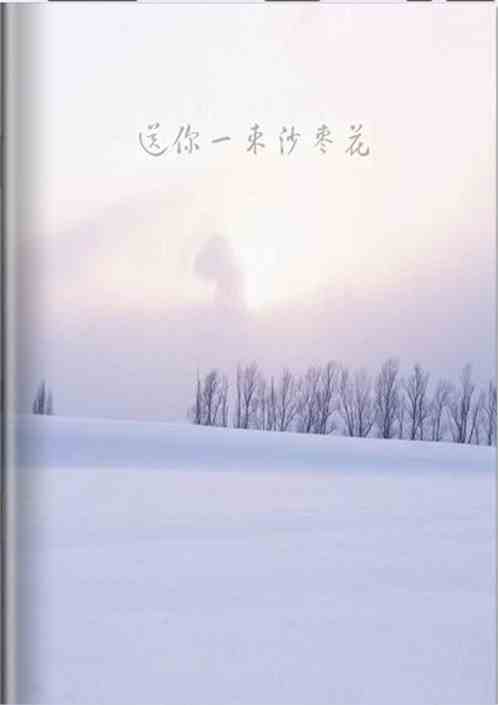《送你一束沙枣花》随笔两则 免费试读
村子里做饭产生的烟
出村后,我前往戈壁滩,茫茫平原上却看不到一个人影。终于,我累了,斜靠着一个角度和一个位置,目光飞快地跑过那些蹲伏着光秃秃的石头的山丘,最后落在了郁郁葱葱的村庄上。当我双脚疲惫,思绪疲惫,天色渐暗的时候,我不会再走很远,以这样的姿势看着远方的村庄。
这个季节已经过了冬天,戈壁上还没有下过一场雪,但是空气干燥而寒冷。走戈壁,是因为在炕上坐久了。经常看书。一方面是想学点技巧,另一方面是喜欢书里的天真。我们这里冷得不正常。我们心里至少要有一个故事,才不会觉得自己不行!我一般不会轻易看书中的故事。心里有什么感觉,就穿上外套,一个人去戈壁。
在温暖的春夏黄昏,我曾独自走过这里。春天来了是因为冬天太冷了,父母真的很担心我的学业,所以我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,去很远的戈壁,在空旷的地方放松,寻找春天的痕迹。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南山山下。这是一个凹陷的地方,有潮湿的沼泽和优良的草地。在那些毛茸茸的草叶下,有天然的泉水,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,悠悠流淌,慷慨大方。好在水里还有一条一寸长的草鱼。北方水少,两条鱼都很让我吃惊。破冰大块,躺在牛羊踩过的水池边,钓两条鱼,春天近了。夏天,除了抓鱼,更是我心情的延伸。为了找工作,为了等很久没有一份爱,或者为了我日益陷入困境的家庭,我不得不来到这里,默默地在戈壁滩上跑来跑去。天空很安静,悬在头顶不说话,地面和天空一路交汇到遥远的天边。只要我还有力气,远方在我脚下从未重复。多少力量,多少思念总会涌上心头的悸动和喘息?人生就像一条遥远的河,静静地流淌,走着跑着不会带来所有的烦恼。当我的心累了,我会回到从前,生活依旧。
我已经可以看到黄昏时村庄的样子了。歪歪扭扭的房子就像抽了一辈子烟的老太太嘴里的牙齿。从干枯的树枝上看到房子,炊烟袅袅,笼罩在村庄上空,形成一团污浊流动的云,久久不散。谁家的狗叫个不停,好像在互相窃窃私语诉说着夜晚的到来,但狗叫声并不押韵,只有几声马上就停了,谁家的女人也在院子里大声说话,好像在吼着贪玩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去睡觉。明明天黑了,还是抹不干净的灰墙,让人心情沉重,深吸一口气。寒冷的空气混合着柴火和牛羊粪燃烧的味道,已经是晚上了。
我心想,我妈跪在墙边,把一把把小麦草往炕洞里塞,用袖子护着火柴一次又一次地试着点燃小麦草。风有点大,胸压低了点,差点把身体填进去。我再一次低下双手,小心翼翼地划着一根火柴,像喂孩子一样轻轻地递了上去。小麦草止住了火,突然轰隆一声点燃了。大火反映了我母亲的寒冷。烟从烟囱里冒出来,火炕慢慢升温。一躺下,眼皮就粘了,睡得很香,做梦的时候嘴里的味道都是甜的。我心想,这时候我妈肯定已经把饭做好了,等着我回去。我亲手擀长寿面,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来,浇上两勺蔬菜汤,端上桌,自己不吃,灶下柴火冲我笑。此刻,她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我。她可能把水温加到锅里了。
此时此刻,村子里特别亲切,我迫切需要回去。我知道,只有在那温暖的炕上,我才能睡得安稳。没有什么比吃一碗妈妈做的饭更好的了。耐心听她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并让她举起勺子往碗里倒两勺清汤,吃两碗温热的食物。睡在她滚烫的炕上太美妙了,外面冷也无所谓,于是我把所有的烦恼抛在脑后,大步回家。
他们
吃完饭准备和朋友离开的时候,朋友看到扫垃圾的阿姨,说:“你说那个阿姨多可怜啊。”我期待着他的手势。一个矮个子中年妇女一手拿着扫把,一手拿着簸箕,跟着几个年轻人把扔掉的纸屑扫进簸箕,转身倒进垃圾桶。忙于生活,更多时候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对别人保持着什么样的心态,就随口说了一句多可怜。
你想家吗?他问。
我说我不想。
他低下头说,我想妈妈。每当我看到那些老年妇女,我就想起我的母亲。他说他晚上看了一篇文章。一个学生上课的时候,看到外面工地上有个女的爬上爬下,突然哭了。老师问她为什么哭,她站起来说头疼。我说我懂,这是一个好故事,一个值得很多人看的故事。
早年出来的时候,一个人走在城市的大街上,找不到工作。看着城市狭窄的天空,我常常问自己,以后会怎么样?走在街上很苦,从希望到失望,从失望到无奈,常常感叹人生。人生很长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离开慈爱的父母,踏上社会,像一粒谷粒。天宇的辽阔,常常让我深深地找到自己的位置,也让我更加怀疑,在未来的某一天,往往是在那一刻,我遇到了更多在城市里流离失所的人。他们衣着暗淡,甚至长短不齐,脸上布满皱纹,头发凌乱,不愿在装着脏尼龙袋的垃圾桶旁徘徊。他们的眼神仿佛泄了火,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平淡,无助,死角,那种目光,有时候会带着乞求的眼神跟随着那个人,停顿又停顿,比那个在看的人更难摆脱。一旦他们找到罐头,他们就把它捏紧,扔进袋子里,然后走开。这时我想,这可能就是我若干年后的样子。当我这样穷困潦倒的时候,我会死的。同时,我记得我父亲也是这样的。为了我们的学业,也为了那个家庭,他粗暴的脱下了人形,但他依然奋力向前,分分钟赚钱。他从不抱怨他们想要什么,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这幅画像是用简单的钢笔潦草地画出来的。
一个朋友说,他妈妈在工地上班。她想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容易。她太刻薄了。当她看到那个阿姨时,他想知道她妈妈此刻在做什么,吃了没有。
他说的话太强烈了。快两年没回电话了。我是对家庭的逃避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接他的话。脑子太乱了。我只是觉得都是这样的。他们种田,干活,干活,我们帮不了他们。这是一种生活,属于那个层次的生活。他们将会受苦,而且他们将来还会继续受苦。它是什么样的?这是生活和角色赋予他们的负担。一旦被扛起,就再也放不下,直到他们再也做不下去了,没有力气了,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休息的时候,就不用承担所有的艰辛和负担了。